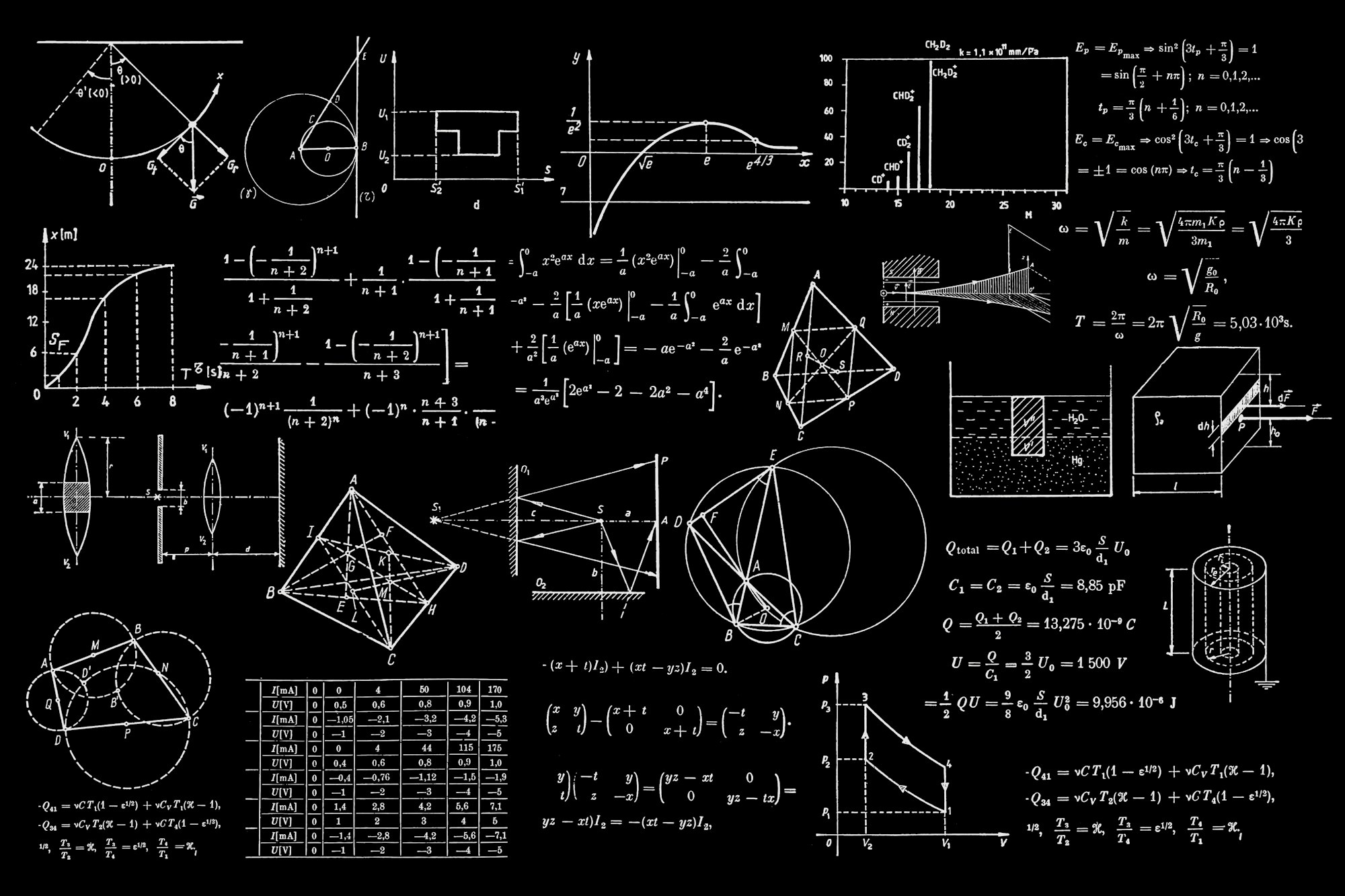今天是七月一号,党的生日,特地先祝党生日快乐。
党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党作对的事情更多,否则我们现在的生活没有道理比一百年前好这么多不是吗,同样的国家的地位没有道理比一百年前高这么多。
世界尚未解放,同志仍需努力!
以下正文:
这一篇继续讲中国革命的独特性。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六 中国革命极端曲折的历程导致政治权力的地域性基本被消除
之前我在分析困难性的篇章里面已经指出,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地域化的问题,表现为各地区的军阀割据以及连名义上的中央蒋介石集团的权力基础也有很强地域性。这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整合国家之困难可能不亚于帝国主义的外在压力。即使侥幸获得了明面上统一的国家,如果不以强力抹平政治权力的地域性,未来的发展也会受到极深的拖累。
我们看一看国际上的情况。能有资格和中国比的主要国家也就是苏联、印度、美国这几家了,其他的规模都太小。苏联和印度的政治权力地域性问题显然是远比中国严重得多。即使是美国,虽有最长时间的建国史来逐渐抹平地域差别,但直到今天它依然有极为深刻的红州与蓝州之间的地域性政治张力,
严重制约了衰落期美国的国内改革和国外政策。和上面这几个国家比,中国政治权力的地域性问题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
关于这一点,只要想想中国大陆内部不同地域间所谓政治矛盾在中国政治讨论中的排位然后再和美国政治中的红蓝州和摇摆州议题热度比一比就知道了。或许还会有人说存在“山头”的问题,但现实早已证明“山头”远比地域性权力来源问题容易处理(还是与苏,印,美,民国比比吧)。此外还要注意,中国这个局面的维持并不是基于高层的来源在地域上均匀分布(这本来也是一种苛求了),这说明有更深层原因。
这种在广土巨族中很大程度上抹去政治权力地域性的奇特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呢?来自于中国革命的特殊历程。
首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有五湖四海不重地域性的特征,
但真正把这种愿景落实的还不是意识形态(否则苏联会做得更好),而是具体实践。由于北伐基于南方以及苏维埃国基于南方,
在长征之时共产党的政军上层有大量的南方人, 他们中很多成为了未来的党和军的上层。延安时代他们又必须在北方全力扩充自己的基层。
经过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发展,到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上层很多南方领导而下层大量北方军民的这种南北合力的超强跨地域组合。
抗战后大量干部进入东北协助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大量南下干部跟着部队进入南方和西部与原先的本土干部结合。 经过了来自东南西北贯通上中下层的几轮大混合,到了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意识形态上而且在现实状况上具备了可以强力抹平政治权力地域性的基础。
很多人会认为中国能够比苏联、印度、美国更能做到政治权力的地域性一统是中国大一统传统决定的。我承认中国的历史传统有深刻影响,但历史传统绝不能决定上述格局的出现。 这是因为中国强有力的大一统王朝往往都依赖于一个建国的军事贵族集团。从大秦的关中集团到满清的八旗集团都是这样子的,而这个集团有很强的地域性。 与此同时,可能还会有另外的基于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其他地域性集团与这个集团相辅相成或者相互制衡,比如明清时代的江浙集团。 这种依赖于一两个地域性很强的集团来长期统治维持大一统的手段在古典时代是可行的, 但是如何转型到现代社会是绝没有现成答案可供遵循的。而且即使在古典时代行得通,内部的代价也是非常之大的,比如极易形成严重党争。总之,很多人明白中国要重建大一统,但这还是浅层问题。深层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大一统,这是中华传统文明里找不到答案的。
中国革命以一种前人很难想象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荡平了中国政治权力的地域性。之后各种有意无意的安排又使得这一局面可以长期维持。到了今天,与外国比,中国大陆内部没有出现“保守派地区”和“自由派地区”的激烈斗争(这个说法本身都有点违和感,对不对?),哪怕内部经济发展是长期严重不平衡的。这令很多外国观察家困惑而又失望。或许还有人想说自治地区如何如何,但仔细想想其权力架构其实是顶层设计的,权力源于全国人民而不是国家一隅,实践早已多次证明如欲实施各种重大政治举措在法理或者实操层面并无大的障碍(也远比其他国家容易)。时至今日,与传统朝代比,中国没有出现湖南集团或者四川集团或者江西湖北“军功集团”,困扰中国至少五六百年的江浙政经学集团搞结党恶斗并常把江南本位看得比全国利益重要的问题在共和国也得到了解决。
中华大地上的“大一统”进程在信史中有三个关键发育期。第一个是西周,形成了“天下,华夏,王土,王臣”等观念;第二个是秦,出现了郡县制的实践;第三个是共和国,造就了大体上抹去政治权力地域性的格局。而且如同秦汉的变革领先世界一样,这次共和国同样领先世界。 西方有句政治名言“all politics are local”,被很多西方人视为基本政治常识,但中国是例外,已经超出他们的政治想象了。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七 在解决中国的民族和边疆问题方面中国的革命者凭借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出色的实操能力以极低代价极迅速地取得了极好成果
我之前曾经分析过,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民族和边疆问题。 既有严重领土撕裂的风险,又有为了阻止严重领土撕裂而爆发对外战争的风险,还有在此过程中结下长久民族仇恨的危险。
现在我们看看革命者的工作成果如何。
除了责任完全在于民国的外蒙古损失之外,绝大多数边疆领土都守住了。 虽然也有一些反叛的行为,但总的说来没有爆发民族战争,也没有造成深的民族仇恨。不仅如此,出色的民族边疆工作还使少数民族在中国对外的武装斗争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东北的朝鲜族显然对中国抗美援朝有很大助力;又如云南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是如此之出色,不仅将长期对汉人戒心极重的很多少数民族吸收进了社会主义大家庭获得跨越式发展,
而且没多久就成为中国往东南亚强力输出革命并在越南和美国苏联接连下大棋的坚实群众基础;
又如西藏地区的成功接收和成功改造使得60年代初中国对印作战时得到了很多西藏边民的有力支援。在对外战争方面,新疆内蒙云南东北西藏都在没有打外战的情况下拿下了,虽然后来有对美对印作战,但彼时已经不是解放和统一战争了,而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作为棋手的大博弈了。
和中国历代控制新疆西藏付出的代价比,共和国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是奇低无比的。再比一比有资格和中国比的几个大规模多民族国家:苏联、印度、美国。显然中国国内的族群关系要远好于这几个国家。
能做到这一点,首先是中国接受了共产主义当中淡化民族矛盾而将阶级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判断。大的方向掌握对了,才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很低的代价把这么广阔的边疆都控制好。另一方面,光有正确的以阶级叙事替代民族叙事的大方向还不够,还需要强大的操盘能力。尤其是因为中国面临着时间极为紧迫的问题(这在之前已经仔细分析过),操盘者不仅要追求低代价还有追求快速。
回想一下的话,中国的革命者在操作时是针对不同地区各自采用了符合当地区情的特色手段。
比如朝鲜族和蒙古族是中共在建立全国政权之前就与之有深度同盟关系的,自然这些地区的控制就比较顺利。
满族是前清的遗族从而长期承受汉民族主义者的压力,并且由于伪满洲国的存在而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被清算风险(不妨想想斯大林风格的对满洲国清算会是什么样的),
但我党无论是在东北还是在北京都没有做为难满族的事情,
没有打断势头已经很好的满族与主体民族深度融合的进程。在新疆方面,中国首先是搞定了和苏联的外部关系从而确保自己能够获得解决此问题的良好和平环境;
又通过统战工作和生产建设兵团等综合手段有效接收和改造了这一地区。 西藏的例子尤为精彩:打,谈,和,拖,改,斗,多种手段齐下。
这种操盘能力固然令人眼花缭乱,但本质上也是党在之前极为复杂的斗争环境下磨练出来的。就以统战工作为例,共产党也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如何做得很好的,有时候连自己人都团结不好,在和少数民族打交道的过程中甚至有西路军失败那样的案例。但在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斗争中,党的统战水平不断提高。 当你已经有了统战抗战期间地主乡贤,有马列之心的日本兵,有抗日之心的土匪,有中立自保之意的伪军,不喜欢共产党但又更担心国民党的中间派民主人士,有投共之意的前反动派等等各种人物的经验后, 再去做民族宗教统战工作也就没那么难了。
总之,我认为建国初的统一万里边疆固然波澜壮阔,但很大程度上是中共深度自我改造后水到渠成之作。正如我前面所说,革命者选择了一条极为艰难风险极高的路线, 但一旦走通了那么很多以前觉得难以处理的问题或许也就迎刃而解了。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八 中国革命者创造性地解决了革命工作军事斗争和政权巩固中的经济问题
在之前的困难性分析中,我指出中国近代面临着极为严重的生存资源稀缺问题,从而导致革命者陷入多难境地。 靠武装先打出去解决经济问题不行,埋头搞好经济再打出去也不行,依赖于外部列强资源则后患无穷。 那中国革命者是如何解决经济问题的呢?
一开始共产党也比较多地依赖于外部资源,甚至到了1938年陕甘宁边区经济收入的一半仍来自外援。但在1927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根据地经济学。 首先当然是在南方的苏维埃国使用,然后带到了北方并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扬光大, 一举解决了革命工作和军事斗争中的经济问题。
这个解决之道有下面几个主要特征。
第一是通过非常特殊的军政军民关系来极大降低军事化动员的成本。
这一点在上面关于军政关系的条文中已经解释了。
仅仅是这一条就已经很了不得了,世界上能够玩转这一套的没有几家。即使是苏联,它在动员成本方面也是难以与中国革命者相提并论的,这和他没有搞好农村工作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了他靠着战时共产主义以及各种强制性很高的手段依然可以完成动员以及完成工业化和卫国战争这样的伟大任务,
但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非常大的副作用。而相比之下,中国革命阶段的这种持续二十多年的高强度长期动员并没有留下什么大的副作用,其经验反倒成为了未来中国发展的宝贵财富。
第二是开辟了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深度挖掘经济潜力的通路。 这本身不是了不得的事情,各国都可以干,真正了不得的是中国革命者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
这里的调整生产关系,最集中体现于土改,它极大地推进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也为建国后的经济巩固提供了巨量的物资保障。不仅如此,即使在出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需要而不能像后来那样铺开来搞土改的抗日战争阶段,中国革命者通过调整生产关系而挖掘潜力的能力也是很惊人的。抗日战争阶段的经济更为困难,而为了统战不搞土改导致调整生产关系的余地相对更小。但即便如此,共产党依然通过种种手段(从自力更生的大生产运动到减租减息既调动积极性又避免破坏统一战线等等)
实现了基本上靠自己解决经济问题。
从苏维埃国到抗日根据地的实践证明,中国虽然贫穷破败但仍有巨量潜力蕴藏于巨量人口之中可供开发,最主要是要做到两条:调动积极性和增强组织性。注意,要做到这两件事都是要大大增加治理成本的,如果做到之后不能收获足够大的经济红利则之前的付出就付诸东流甚至会反噬自身。这里的最大难点(假设组织力动员力已经足够的前提下),我感觉是预判到底能挖出多大潜力而不崩盘。有了预判力,才不至于开发强度太低(这是很多亚非拉国家的情况)或者措施太过火造成极严重后果(苏联农村工作就有过这种问题)。
那么这种预判能力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觉得是苏维埃国和长征帮助革命者探查了自身的极限。 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虽然也辛苦但我想经济条件比起长征时应该还是更好的,可能经济情况也不会比苏维埃国糟糕很多(即使比苏维埃国糟糕)。既然以前都挺得住,那么经过长征锻炼后成为革命骨干的数万老红军心里就有了底。很多观察者都注意到,延安时期不管再困难气氛都是颇为乐观的,这和苏联动辄慷慨悲壮不是一个风格。 我想可能关键就在于”再难也远没有长征难”。我尊重苏联的精神,但我以为中国的境界更高。
再有,苏维埃国的经济工作经验也很重要。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实践根据地经济,成就不小,失误也很多(尤其是一些过激政策)。苏维埃国虽然失败,但带着经济工作正反经验的很多骨干活了下来,第二次于陕北华北实践时他们就成熟得多了。可以说,中国的广阔空间使革命者获得了较多的试错机会,所谓大国战略纵深这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再多说一句,我觉得中国的此种大国“试错纵深”比苏联还深厚,虽然苏联地域更广。比如说我很难想象苏联革命者把莫斯科-圣彼得堡政权搞失败后还有跑到偏远地方再起的机会。
中国革命遭受过反复惨败,后来胜利的共产党则两次严重挫败。这固然是损失,但所谓“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两次命悬一线后又能整装再出发的共产党革命队伍不仅有人民的力量,理想的力量,真理的力量,还有重生的力量。这最后一种力量是其他很多国家包括苏联的革命者都不具有的。
第三是高度重视并逐步玩转了匮乏条件下的实物经济,从生产到流通环节都有丰富经验。 当然这是客观环境造成不得不如此,但在高度重视实物经济中尝到巨大甜头之后,中国就形成了利用超强的动员力以及实物经济实操能力去和更加现代的经济体系融合或者对抗的自信。这一点大家比较熟悉,我就不多讲了以免这一节篇幅过大。
到了革命快要胜利的阶段,中国革命者在强大的根据地经济的基础上又快速而卓有成效地搞好了一个二元经济体系,即城乡二元经济。
考虑到在接收大城市之前中共没有在大城市搞经济工作的经验, 他们能够在解放战争后期到建国初期把大城市的经济工作搞得如此之好其实是令人震惊的。
从东北开始获得部分工业城市后就能很快恢复交通以及相当多重工业和兵工厂的生产从而有力支援后来的解放战争乃至朝鲜战争。
这个已经是不错的初级工业组织能力了。而在接收了上海为代表的广大南方地区之后,则面对积重难返的蒋介石集团留下的经济烂摊子在短期之内就摆脱困境。到了53年左右,全国经济工作格局大振,各方面预言或者担心的把城市经济搞砸的情况没有出现。
而这一切是在中国还在朝鲜进行激烈作战以及在国内四处剿匪镇反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个过程中,既有大家津津乐道的手段老辣的上海经济战,又有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货币统一和新旧货币平稳过渡转换。我党在长期农村工作和根据地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竟然也培养了一批一上手就能搞好城市经济工作的人才,这种人才储备和培养能力也是叫人匪夷所思的。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做到的,也就不进一步分析了。
只有把建国初那几年的经济工作做得那么好,中国后来才有可能比较顺利地接下苏联的大规模经济援助和工业输出并开始五年计划,也才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快速完成后来的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这是不亚于抗美援朝的大事,但时常为网络议政者所忽视。
当然大家都知道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是遇到过很多困难走过很多弯路的,但是这不能用来贬低中国近代史阶段革命者的经济工作成就。 而恰恰是中国近代史阶段经济工作的巨大成功,为中国未来的困难和弯路阶段积聚了很强的抵御能力。
比如农村被打造成了很强的经济蓄水池和缓冲网,又比如城市工作方面基本上能避免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再比如,在以较弱的国力进行一度与美苏同时对峙的冷战大棋局的过程中,在进行工业化原始积累的过程中,
中国虽然财政严重紧张了几十年但没有被财政问题压垮也没有陷入还不清债的局面,这和建国前在极端条件下长期运行的积淀分不开。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九 中国革命打造了一套独特的意识形态
这套意识形态我指的就是毛泽东思想。 它是中国自主形成的,是将外来重大思想资源本土化的, 是与实践并行发展的成体系指导思想。
后发国家在救亡独立和转型的过程中需不需要成体系的意识形态?需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如何形成这样的意识形态?这些是革命者必须解决的重大基本问题。中国的解决之道有如下几个独特方面。
第一, 新意识形态是建立在对深厚文明传统中落后部分的深刻批判和坚决扬弃之上的。 从打倒传统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的统治地位到掀翻长期在民间中生命力非常顽强的各种迷信和宗族势力都是如此。
这种力度的涅槃重生意味着新生的体系将是受古典时代思想拖累最轻的从而是最现代的。
这一点在中共之前甚至中共之外可能没有一国能做到。比如各个先发国家都保留了大量宗教残余,后发国家保留的古典时代残余只怕更多。哪怕是苏联,从近几年我看到的解释看,与传统的决裂也不如中国深。
第二,新意识形态建立在对居于指导地位的外来思想进行坚决改造的基础上。中国革命的成功当然有赖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但无论是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还是经过列宁改造后已经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列宁主义,都不能回答中国革命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 要正确回答中国革命该如何进行,就必须要做出一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意识形态改造。
在本国的很多深厚传统已经被扬弃的情况下, 对于外来先进思想还敢于做如此深度的改造,这里需要的勇气是非常巨大的。而改造能够服众,归根到底也必须依赖于实践中的成功。这就指向了第三个特点。
第三,中国革命指导性意识形态是在压力极大的革命实践中依托稳定核心而逐步形成的。
历史上有很多重大社会转型非常漫长并因此没有很系统化的意识形态指导,比如西方进入近现代资本主义。有的重大转型则是事前有了很系统的意识形态从而速度很快,比如俄国革命之前就有列宁的重大理论突破。
而中国的情况与上述都不同。 毛泽东思想虽然在1927年之前有一些早期的部分,但其主体部分是1927年开始建立革命政权的实践之后才发展起来的。这种一边打仗一边搞根据地建设一边改造外来先进思想一边发展自己思想既用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再用新的实践来支持新的思想的模式,是很难操作的。因为这要求一个相当稳定的思想核心,而这个思想核心必须既有强大的学习能力,还要有强大的思想建构能力,与此同时还必须有重大的实操能力,如此才能做到学,思,改,行合一的境界。
第四,中国革命指导性意识形态形成并取得重大胜利的时间是很短的。从共产主义在中国大规模传播到毛泽东思想进入党章不超过30年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不仅完成思想体系的构建而且用思想体系武装了数以百万计乃至上千万的钢铁战士建立强大政权,效率实在是惊人。 我觉得人类历史上可能只有伊斯兰文明崛起之效率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立改造外国先进思想基础上的指导性意识形态之后,就拥有了惊人的政治思想底蕴。这个底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未来摆脱外来意识形态源头(苏联)的束缚走向政治与外交的彻底独立有了坚实的基础。第二,为将来吸收和改造其他外国先进思想(改开以来学习西方)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至少使得后来人觉得这件事是做得通的。第三,这种发展和改造指导思想的传统也为后来人对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形成的传统做进一步改造提供了先例。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十 中国的革命者具有极强的分析外部形势和把握重大外部机遇的能力
其实革命者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这种能力的。中国革命的两次重大挫折(1927大革命失败和苏维埃国反围剿失利)都和分析外部环境时有重大失误是密不可分的。 但是在遵义会议以后情况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是找到中央军和各路军阀之间博弈的缝隙,成功摆脱多次包围。其次是快速坚决地通过零星情报在陕北找到了合适长期立足之地。 再往后虽然有西路军这样的失误,但那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与外界博弈时犯的最后一个重大错误。 从西安事变开始,革命者领导集体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斗争的重大正确判断和决策。
这些重大正确判断和决策包括:
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在37-38年判断华北出现重大权力真空, 全力往华北扩张并继续坚决走之前已经走失败过一次的农村路线,
正确分析日本力量的限度,提出持久战战略, 在华北扩张时采取正确的统战政策,在国民党掀起以皖南事变为代表的反共高潮之后有力地以斗争求团结,
正确判断卫国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形势,利用重庆和谈和马歇尔调停为自己争取战略时间,及时派大量精干力量进入之前力量较为薄弱的东北地区,在东北正确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敢于放弃延安与敌冒险周旋牵制敌人大量力量(可能也造成蒋的很大误判),刘邓大军挺进蒋介石统治腹地,及时发动辽沈淮海战役(不仅仅包括国内战局的把握也包括国际上抓住美苏陷入一年多柏林危机抽不出手的关键机遇),以打谈并举的手段解决平津问题,
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不惜长时间停留莫斯科来获取一份对当时的中国较为有利的中苏友好条约,
执行一边倒的对苏友好政策并利用此政策保障的战略时间快速解决西北青藏和南疆问题以及彻底没收帝国主义资产等,
做出冒险性极高的参与朝鲜战争决定并取得重大胜利, 既敢于对英帝国主义开炮又坚决保留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及时介入印度支那事务援越抗法,等等。
总之我认为从1936年西安事变后到1953年(即我划分的中国近代史的终点),中共在对外博弈方面没有犯过一次较大错误。这段时间正是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上列国博弈局面最为混沌和政治家决策压力最大之时。苏,德,日,美,英,法等世界主要玩家都犯过大错误。但中共却交出了可谓“零失误”的答卷。
尤其难得的是这里面的很多决策都是中央位于地理上极为闭塞的西北内陆或者华北小村之时做出的。 他们如何在这样的闭塞条件下具备这样强的时局分析判断能力?
我想这归根到底取决于两个要点。两个要点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毛泽东和周恩来。
第一个要点,就是有人具有很高的站位能够跳出一时一事的进退得失来看出大道理管着小道理。第二个要点就是中共始终具备非常强的情报能力。
第一个要点前面已经说过很多。关于第二个要点我再多说几句。
从打入国民党内部高层的各种特科特工人员,到潜伏在广大城市里的大量地下人员,到有可能在美国(甚至苏联?)也有相当情报收集能力的人员,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掌握着一张强大的情报网。没有这张网,纵有正确的宏观判断,在战术执行上也很可能陷入很多麻烦。
这种在混沌环境下在强者力量边缘进行激烈博弈的成功传统当然是首先从毛泽东指出为什么如星星之火的小型革命政权可以在军阀混战的中国存在开始, 之后在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中这一传统被发扬光大。其实这一传统也被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成为中国革命者又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转]:中国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三)](https://images.unsplash.com/photo-1583405584623-58f4b7d1380f?crop=entropy&cs=tinysrgb&fit=max&fm=jpg&ixid=MnwxMTc3M3wwfDF8c2VhcmNofDF8fGdyZWF0JTIwd2FsbHxlbnwwfHx8fDE2NTM1Njg3NzQ&ixlib=rb-1.2.1&q=80&w=2000)